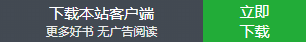要查这个,倒也不难,村子不大,在查文斌去的时候,村东头确实有人自缢了,大约是在一个月多前。
村东头有一户人家,户主姓余。老余有膝下有三个儿子一个姑娘,老伴儿死的早,他一手靠着自己的篾匠活拉扯大了四个孩子。
浙西北产竹子,这儿有着大片大片的竹林,靠山吃山的农民们从这种韧性绝佳的植物身上发明了篾,从竹篾做成的箩、篮子、桶、匾等等生活用具一直延续了上千年。老余就是靠着一把篾刀硬是养活了一大家子人,竹篾多倒签又是异常锋利,干这行,靠的完全是手指的力量。也正是因为如此,老余的手指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就不能做到弯曲了,等五十岁的时候已经是基本残疾了。肿大的关节、粗糙的皮肤,厚厚的手指甲,刀疤贴着刀疤让他的双手伸进热水里都感觉不到温度。到了冬天就是老余最受罪的时候,他的手指和手掌便开始会开裂,露出里面鲜红的肌肉,只能用毛巾包着。
就是这样一位老人,先后给三个儿子造了三栋新房,娶了三房儿媳,最小的姑娘陪嫁的时候那也是在村里不落下风,可以说,他这一身的心血都花在了儿女身上。
而他的三位儿子如今都已各自成家,要说这人到晚年,儿孙满堂正是他老余该享受的时候了,辛苦了大半辈子拉扯后人,现在是轮到儿孙们孝敬他了。
可现实生活中的确有那么一匹不孝子和白眼狼,老大发话他是最早成家的,老余应该归两个小的管;老二发话,自己家屋子小,住不下;老三发话,他是最小的,养老的问题应该归哥哥。可怜老余辛苦一辈子,人到黄昏时被三个儿子跟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,唯独小女儿偶尔把老人接回去住,可毕竟是嫁出去的姑娘,老余好面子,不想给她添麻烦,自个儿回了老屋肚子单烧。
年纪大了,手又残了,老余已经没办法再干篾匠的行当了,家里的田地又早早给三个儿子分光了,他唯一的财产就是这三层的土坯房。因为年久失修,常常外面下大雨,里面下小雨,一个土灶,一张他结婚时的床,两个木头箱子外加几把篾刀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。
老余年轻的时候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老实,不料老了却落了这么个下场,村里的人看不过去,有热心的就隔三差五的去送点吃的。村里为他的事也找三个儿子协调过,几番都没成功,就为了他办了低保,只能买点米勉强糊口。
最大的难处其实还是伤病,即使有了米,老余的手也很难弄到一口热的吃。这样作孽的日子过了有三四年,到了那一年的开春,村里要搞竹木加工厂,老余那老宅子要被征用。
原本从不往来的三个儿子一听要拆迁,天天都往老余哪儿跑,三个儿媳恨不得雇轿子把老头往自己家里抬。其实老余心里明白,这是他们惦记着那点拆迁款。村里的干部也考虑到了他的情况,说是给老余重新挑一块地盖平房,剩余的钱就留给他养老用。
那三个儿子整天去村委会闹事,闹的人是工程也开不了,最后老余出来妥协了:就给钱吧,房子不要了。他这样做,是为了不给那些照顾他的干部们为难,老余是个好人。
钱自然是没有进了老余的口袋,三兄弟为了怎么分这笔钱大打出手,菜刀锄头都用上了。那天也注定了和平时有些不一样,四五月的天气,大中午的浙西北竟然罕见的飘了一阵子雪花,天空阴沉的有些可怕。老余的身后是三个儿子鼻青脸肿的互相叫骂声,儿媳之间的撕扯声,还有钞票哗啦哗啦的响声。
中午的时候,有人看见老余拿着他那把篾刀进了林子,下午两点的时候,工程队准备去拆房子,打开房门的时候看见老余吊在一根麻绳上,双脚直挺挺的。他的脚下是一口棺材,那是很久之前他还用能力的时候从外公那儿定的,棺材两边各放着两根抬杠用的木头,用红纸糊着,所有的一切他都给自己准备好了。
那是一身已经洗的发白的蓝布中山装,补丁补的相当不专业,据说这是他结婚那年买的,也是他唯一一套拿的出来的衣服,但是很干净。
老余就这样走了,他的葬礼办三个儿子都要出头办,因为在那儿白事是有份子钱收的,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,为此事,三兄弟又大打出手,但是却没有人为老余流过一滴泪。
查文斌没在,这丧事自然也就没有道士做场,按说这样的非命是一定要请人来的,但是为了图省钱,能免则免,就连寿衣老余都没捞着。最后,老余下葬了,剩下那两根抬杠的木料都被儿子给卖进了木器厂,绳子则在半道就给丢了,不想就这样阴差阳错的被超子捡了去。
说出这件事的,是村里的张嫂,她是老妇女主任,也是负责给老余生前送米送油的。查文斌自然也是认识他的,因为过去他也会问老余定些东西,比如他常用到的灯笼都是老余给做的。
就连昌叔听完了张嫂的陈述都用拳头敲打着桌子一个劲的咧咧道:“不孝子啊不孝子,遭雷劈的啊!”
查文斌向来是不喜欢管人家家务事的,但老余的确是走的太冤了,特别是张嫂跟他说老余死的时候眼珠子瞪得老大,怎么合都合不上,看得人心里发毛,最后他那小儿子用黄纸盖在他脸上才算了事。
本章未完,点击[ 下一页 ]继续阅读-->>
【本章有错误,我要提交】【 推荐本书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