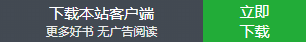下朝后,林文轩就把明阙送回了武阳侯府,因着两家也算有恩怨,他倒也没多做停留,把人交给了武阳侯府的下人便离开了。
侯夫人收到消息急忙赶到明阙房间时,正好看见下人捧着带血的衣衫出来,她登时慌了神,忙冲了进去,「怎么了怎么了,好好上个朝,怎得伤成这样!」.z.br>
明阙刚换上的干净亵衣,不多时又染上血色,他脸色苍白,却害怕吓到母亲,只得低声宽慰,「娘,我没事,你别担心了。」
「还不快去请大夫!」侯夫人眼含热泪,吩咐完下人,又坐在床边拭泪,「瑨安,你这孩子……」
还没来得及说两句话,得了消息的武阳侯也匆忙赶了回来。许是路上听到了什么,脸色算不得好看,「行了,你去吩咐下人打点热水来,再去看看大夫到哪儿了。」
二人做了多年夫妻,自然知道武阳侯这是有话要对明阙说,侯夫人即便再想知道原因,眼下也只能忍下来,带着丫鬟下人们出了明阙的院子。
武阳侯年近五十,膝下子女众多,自己虽算不得中用,但有祖上荫封庇佑,日子过得舒服,人到中年,不免松了皮肉,比起权贵,更像个富贵闲人。
「你今日很不该公然和方知野作对,你明知他——!」
「明知他权倾朝野,明他是太后的人!难道就由着他败坏朝纲,在朝中兴风作浪,连累无辜百姓吗?!」
武阳侯一开口,明阙就知道他要说什么,扬声打断了他的话,语气里多了几分壮志难酬的苦闷,「父亲,儿子读书多年,登科入仕不是为了助纣为虐!」
明阙越说越激动,还没上药的伤口又崩开,沾了一腰的血。
到底是自己的亲儿子,武阳侯怎能不心疼。
他一把摁住明阙,不许他再乱动,「可你这样分明是要拖累全家去死!」
「还有你的这封折子!」
武阳侯脸色铁青地从袖子里掏出一封奏折,「你竟然还想替宋家求情!」
「宋清正的罪名乃是三司会审陛下亲断,宋清正坟头草也已有丈余高,你这个时候翻旧账,难道是要我和你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吗?!」
「难道你要为了一个已经死了的旁人的女人,舍弃你的父母家族?!」
武阳侯的每一句质问都如同惊雷,把明阙砸得头昏脑涨,说不出半句话来。
好半晌,武阳侯叹了口气,他提步往外走,待走到门口时才转身冲明阙道:「你这段日子就好好在家养伤吧,朝廷上的事,你就别管了。」
这话摆明了是要软禁他。
「爹!」
明阙想翻身追出去,可后腰传来的刺痛痛意叫他直不起身,而回应他的,也只有沉闷的关门声。
***
「听说明阙在朝堂上公然顶撞太后,被打了板子。」
宋觅娇在客栈待得无聊,让沈自熙给她买了一堆针线布料,她这段日子不是给孩子做衣裳就是绣鞋子,沈自熙也看得手痒痒,不知从哪儿找来几块木料,给孩子做了小木马和木头剑,只等着孩子出世。
听到沈自熙这话,宋觅娇下针的手一歪,把老虎胡须给绣歪了。
「他性子耿直,又被家里护得太好,行事难免鲁莽。」宋觅娇拆了绣错的线,语气平静,「不过这次只是打板子,他若能涨点记性,也算好事。」
她说完这话,也把虎头帽的胡须重新绣好了,正要拿给沈自熙看的时候,却发现那人沉默不语,也不知在想什么。
宋觅娇这才后知后觉地察觉,她忍不住轻笑出声,又凑近沈自熙,拱了拱鼻子,「呀,哪家的醋坛子打翻了,好大股酸味儿。」
「怎么没听你说过,你爱吃酸的。」
沈自熙轻笑着拉住她的手腕,把人拽进自己怀里,下巴放在宋觅娇肩窝,毛茸茸的脑袋蹭着她光洁的脖子,「我还犯不着跟他争风吃醋。」
「如今朝政被太后把持,他仍保持本心,记得为官之责,这点我倒是佩服他。」
宋觅娇握着沈自熙的手,轻轻抚过他这几日做木工不小心添的几条伤痕,「虽说明家式微,但祖上也曾出过三位太子太傅,深受读书人推崇爱戴,太后再是不悦,明面上也不会对明阙做什么,不然就不是打板子了。」
「但看太后的意思,这兵是非出不可的。」
「不说他了。」沈自熙点点头,反握住宋觅娇的手,「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去江南?」
「正好阿寻前日来信,说水患已经有所缓解,我此时过去也合适。」
正如她刚才所说,太后兴兵之心坚决,是不可能再拖下去的,这个时候她若是留在西凉,只怕远没离开安全。
夫妻二人心知肚明,便也没多说什么,「我把步长命留给你,他人虽不靠谱,但好在有一身好医术。迟刃也已经到西凉了,她会一路护送你。」
宋觅娇下意识想拒绝,但想了想肚里的孩子,又想到若是她在路上出了什么事,沈自熙远在千里之外只怕也会乱了心神,倒也不扭捏,点头应下。
既然要走,总得同外祖父说一声。
她要带走步长命,也得把伏古丽身上的蛊虫给解决了。
【本章有错误,我要提交】【 推荐本书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