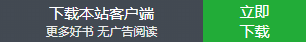一听楚维舟的话,就知道他在江崖霜手里吃过亏——而且还就是昨天的事情,秋曳澜勾了勾嘴角,毫不掩饰脸上幸灾乐祸的神情。
楚维舟恼怒的看了她一眼,向楚维则道:“二皇兄,您怎么和他走在了一起?”话语中对江崖霜的不满,溢于言表。
“我们是在路上遇见的。”楚维则比楚维舟大一岁,今年十八,但性情却要比胞弟沉稳得多。从他脸上丝毫看不出来对江崖霜或秋曳澜的任何不喜,神态怡然而雍容,“三皇弟怎会在此?”
“路过,看到有人喊冤,就停下来看看。”楚维舟阴着脸,“却没想到宁颐郡主口齿犀利,三言两语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,不但反过来要问这对可怜夫妇莫须有的罪,甚至还要问起本王的不是来!”
秋曳澜满眼无辜:“周王殿下这话,我可不敢当!一来我从未问过您的不是;二来这对夫妇究竟是讹诈还是真的受了委屈,我说没经过衙门,不好说,难道有错?”又道,“即使他们真的受了委屈,自有国法为其讨个公道!先过来把‘仁庆堂’砸成这样子算什么事?”
江崖霜立刻道:“宁颐郡主说的很是,国有国法,家有家规。无论何事,总是要按着规矩来。周王殿下偏听偏信,实在委屈郡主了!”
“这区区委屈算不了什么,只是‘仁庆堂’好歹也是数十年的铺子了,上下两代人积累声名不易,就这么被践踏入泥,实在叫人痛心!”秋曳澜微微哽咽。
“唉!周王殿下委实卤莽!”江崖霜同情的唏嘘,打量四周,“这铺子也是民脂民膏啊!”
秋曳澜悲切垂泪:“外祖父卧病在榻,诸样的药都不能断的。阮家如今产业已经不多了,这‘仁庆堂’乃是最紧要的一份,后面库房里就放了外祖父要用的药……我到现在都不敢去后面看,万一也被毁了……家母去年故世,如今我外家长辈只有外祖父一个……”
说到这里,她顺理成章的哭出声来!
江崖霜脸色一沉:“真是岂有此理!到底是不是‘仁庆堂’抓错了药,还没弄清楚,居然连阮老将军用的药都毁了——老将军一生为国,如今病倒在榻,居然还要受这样的侮辱?!这简直就是不把为国效劳毕生的将士放在眼里!!!”
因为插不进他们两个的话里,正在向楚维舟询问经过的楚维则闻言微皱了下眉,走了过来:“十九表弟且勿激动,想来也是这些庶民不知道后面有阮老将军用的药,不然怎么敢下这个手?”
又责备的看向秋曳澜,“这正月里,药铺按照常理是不开门的,阮老将军用的药,为何还放在药铺、而不及时取去将军府呢?如今耽搁了老将军用药可怎么好?这样吧,缺哪几味药材,本王先设法给你补上!”
他这番话不简单,先是把毁药的责任推给那披麻戴孝的一家,给周王脱身;跟着质问秋曳澜不重视阮老将军用的药,老将军用的药居然放在药铺而不是将军府里;继而做好人——
不过秋曳澜自不会顺着他的计策走,立刻楚楚道:“燕王殿下好意,我代外祖父与表哥心领了!实不相瞒,之所以把外祖父的药存在这里也是没办法的事情:将军府这两年家计艰难,除了外祖父住的地方,其他地方都是多年没有休整过了。若把药材放外祖父的住处,药味太浓会熏着外祖父的!要放其他地方,又怕失修的屋子漏风漏雨又漏雪,会导致药性流失,这才……”
楚维则微微皱了下眉,感到有点不妙。
“若非表哥过继到外祖父膝下后拿了自己的银钱来补贴,外祖父这两日的药都吃不上顶好的。”果然秋曳澜还没完,一眨不眨的看着他,很可怜的道,“修缮整个将军府如今是不敢想的,就是只把原本放药材的库房修一下,至少也得五六千两银子——表哥所携银钱也不多,还要给外祖父诊治,实在是……实在是抽不出来啊!”
“郡主何必哀哭?”江崖霜气定神闲的补刀,“燕王殿下不是已经答应帮你了吗?以后老将军的药,再不必担心会失了药性!”
秋曳澜立刻惊喜的看向楚维则:“燕王殿下肯替阮家修缮将军府?!”
楚维舟差点没气晕过去,怒喊道:“你不要太过分!”
“……本王尚未开府,囊中亦不丰裕。”楚维则苦笑着拦住楚维舟,“修缮整座将军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,若只修缮下存放药材的库房,大约还可以。”转头吩咐亲信侍卫,“回去后取六千两银票送去将军府!”
“殿下您义薄云天又平易近人!这叫我无以为报——
本章未完,点击[ 下一页 ]继续阅读-->>
【本章有错误,我要提交】【 推荐本书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