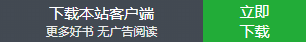大哥大没有想象的沉。青豆掂了掂,又还给傅安洲,忌讳地不再看他:“别乱想。”
坏事不能老提,说着说着会成真的。
“不打一个吗?”傅安洲不放心。
“首先,现在六点,他没起床呢,其次,我跟他说什么,说我刚吐了一下?”她无奈地摇摇头,“太不像话了。”
见她往校外走,傅安洲不放心,跟在后头。
说实话,他有点担心青豆状态。她吐的反应,确实和安清辞怀方子语那会差不多。早上呕吐,闻不得味。
“豆儿。”他唤她。
青豆没有理他。
她想自己骗自己,可身后傅安洲的脚步声不断提醒她,喂喂喂,有个麻烦事儿没搞明白呢。
哎!烦死了!
走到公交站台,上清山的车子迎面摇晃而来。看来是缘分了。你看,这缘分来了,挡也挡不住。
她暗自叹气,头也没回地扎进早班车,傅安洲在关门前,也上来了。
青豆有公车月票,傅安洲没有。他从厚厚的黑皮夹里掏出一张一百的,递给背木箱的售票阿姨。
阿姨这边刚上班,木框子里只压了几张简单的五块十块,不耐烦道,“没有小票子吗?”
青豆扫了眼他那颇为猖狂、纸票厚得压不住的皮夹子,心里又叹了口气,从兜里掏出六毛钱,帮他付掉了车费。
“你随身带这么多钱干吗?”她带一张都嫌多。
傅安洲捏起皮夹,好玩地往她面前一送:“有时候结账要用。”
那钱夹的丰厚程度,足够青豆这样的好孩子生出歹念。黑压压的百元大钞,她得写多少小说啊。
二十分钟左右,城市建筑逐渐矮去,脚手架们出现在郊区边缘。到上清山附近,云彩越发变幻莫测,美得让人有点绝望。
青豆下车,抚心口舒了好一会气,才能继续走路。
傅安洲在香店和袅袅笼屉前犹豫,“要买香吗?你能闻吗?”
他以为青豆是来烧香拜佛,祈祷平安的。青豆说:“给我买两个馒头吧。”
傅安洲问:“要葱花卷吗?”
“不要葱。”她平时爱葱,这几天却不能闻见一点葱味。啊啊啊啊啊……烦死了。
他要了四个馒头,一边掏钱一边清嗓:“那能爬山吗?”
他俨然已经把她断定为一个有身子的人了。要换做平时,青豆肯定要认真解释,别瞎想,但今天,她实在没力气。
“我不爬,我就来找个人。”青豆已经看到他了。像棵树一样,扎在山脚。
青豆不喜欢别人等她。虽然他们没有明确约定,但青豆猜到张数昨天那话的意思是邀请她一起爬山。
她可以不来,但她管不住自己的脚。
她现在啊,真是管不住任何事。
青豆走到张数跟前,递给他一个馒头。张数今天很精神,换了新polo衫,抹了发油,眼镜擦得锃亮,“来了。”他嘴角的笑意放大,朝傅安洲点了点头,“男朋友吗?”
青豆摇头:“不是,是朋友,陪我来的。”
张数点头:“对对,得注意安全。”
荒郊野岭,来见个陌生男人,确实要带个朋友一起。青豆的考虑很周到。
青豆从昨天的情绪里走了出来。她拒绝爬山,跟张数明说,“我哥前两年剃度了,一切都挺好的。”
张数点点头,仰头望向山上茂林掩映中的庙宇:“我就去看看。不打扰。”
青豆说:“他不在这座山。”
张数一愣:“是吗?”
张数不知道他在哪里。
80年的大年夜,他被赶出来,流落街头,后来是走回的姑姑家。一百多里路,一边问一边走,一旦走错,就浪费几公里的脚程。
他和青柏失去联系。他在东城上大学,一年只够回来一次。他写过一次信去北京工业学院,没有收到回音,后来去过程家村找他,不敢靠近,只假装路过的路人,经过那户人家。
那天青豆家敲锣打鼓,请了师傅做法驱邪。他垂头丧气,联想到,自己可能就是那股邪气。
知晓青柏退学是前几年,张数在镇上碰到当年一起在师范高考的同学。对方落榜,上了大专,现在是镇上小学的校长。他说,你知道吗,我们那届第一名,退学做和尚去了。
说时已是物是人非。
张数在上海工作多年,对宁城的事一无所知,更别提南弁镇了。再是沸沸扬扬,南弁镇也只是中国数万个城镇之一。
于是,张数又去了一趟程家村。
和传闻中一样,青柏家没有人,双开木门上落了两把重重的锁。外墙贴着面驱邪铜镜,把他照得清清楚楚。
他没敢问近邻,跑远点问了个老乡,那人说,这家散了。
他不信,又找了个老乡,说法又变了,说这家举家迁往南城,因为儿子在那里。
张数以为,那个儿子是青柏。
青豆没有说大哥在南弁山,而是说:“我过阵子去见大哥,问问他想不想给你知道他在哪儿。”
“你别找他,”张数摇头,“我并没有要打扰的意思。”
他只是想远远看看。最后一面,夜里太黑,他没能看清他,手边也没有一张照片,这成了他多年的心病。此后再与人告别,他都要做那个最后转头的人。
“我不问也要去见大哥的。”青豆懒得与他纠缠,话说明白,转身就走了。
傅安洲像个观音兵,鞍前马后地跟她又回了公交站台,手上还拿着两个馒头。
本章未完,点击[ 下一页 ]继续阅读-->>
偷吃小姨子视频漏出
【本章有错误,我要提交】【 推荐本书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