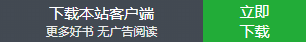伤狱卒、劫囚犯,是件大事。
但银州官府毫无动静,还在失踪人员名单上,添了个小赵。
小赵抱着丝绸软纱衣裳颠颠奔上三楼,见枯坐禅门上仍贴着封条,失落万分。将她带回软玉楼的人说,春容姑娘已回到枯坐禅中,但害了病,需要个丫头照料。她带着对方给的新衣,拎着对方给的草药,满心忧虑地跑上楼,却跑了个空。对方大约是在骗她,只是同她讲了个玩笑话。
她怀中抱着一团衣裳,蹲下身子,样子十分滑稽。呜呜咽咽哭着,怕眼泪弄脏新衣,只能歪头顶肩抹眼泪。
门忽而启开一线。
小赵怔了片刻,急匆匆站起来,撞开门进屋。
“带了衣裳。”清亮却懒散的调子响起,“有我能穿的吗?”
枯坐禅的几扇窗仍烂着,风灌进屋里,一丝热气儿不留。小赵没答话,抱着衣裳直奔床畔,见春容双颊通红昏迷在床上,忙放下衣裳,将破烂窗子半遮半掩地关上。虽仍漏风,却好过敞开着。
关了窗,又慌里慌张在屋内搜罗,找出炭盆炭火,汤婆子、暖手炉也一并翻找出来,烧热了炭,搁在床边生暖,暖手炉塞进被窝里。手刚一伸进去,发觉被窝里潮湿寒凉,又急着翻找被褥。
祝眠被晾在一旁,看她忙上忙下。
一边窗子被风吹得框框作响,满屋子冷风乱窜。没用。祝眠索性拎起一旁木桌,在靠近床畔的床前比划两下,手中劲道一出,桌腿被按进墙里,桌面与墙体严丝合缝,一缕风也钻不进来。
小赵终于停下片刻,一床红缎面被褥压在她单薄纤细的身子上,显得格外厚重。她红着一双眼睛盯着祝眠,带着哭腔瑟瑟缩缩:“祝公子,姑娘她病着,没法子伺候你。”
见祝眠没有动静,她继续忙活。
桌板挡了一扇窗的风,却仍有几扇窗未遮。春容风寒发热,不宜再吹风受凉,身上湿衣潮褥需得尽快换下。小赵拉下纱帘遮风——聊胜于无——再替春容换衣。
褪下衣衫时,乍见春容腹背上青紫淤痕,小赵眼泪止不住地掉,她未料想到衙门会对春容用刑。旧衣摆上全是泥水砂砾,尖锐泥沙刀子似的,在细嫩小腿上留下道道划痕。一双玉足更是惨不忍睹,姑娘们只在楼内活动,楼内所制鞋子底儿都极软极薄,踩上硬石子路,没几步就烂了底,脚趾脚掌都被磨得血肉模糊。
衣裳能换,可伤口也得清理,汤婆子里还要灌上热水。
小赵抬袖擦去眼泪,飞速将软纱里衣给春容套上,又将被褥换了新的,手炉塞进被窝里,掖好被子后掀开纱帘。忍了又忍,开口时才没哭出声来,说了句囫囵话:“是我怠慢公子。但姑娘身上有伤,我得去烧热水。”
祝眠倚着桌板,神游天际许久,听小赵开口后,忽然扯了句无关紧要的话:“包串粽子,甜咸都要。”上午他觉得饿,从药渣子里挑挑拣拣,找出几口能垫肚子的吃了。这会儿已过晌午,药渣子不顶饱,他又饿了。
“厨房的人全被抓去衙门了。”小赵紧张春容的伤病,本就心急如焚,见祝眠不慌不忙还要点菜,说话间难免带些急躁。话一出口,她便意识到不妥,顿时脊背发凉。刚刚太过着急,她忽略了祝眠的身份。
一个杀手。前夜刚刚杀死六人,就在这个房中。若心中不痛快,想要杀她,不费吹灰之力。
“我、”小赵磕巴起来,“我是说,我能包粽子,但是我还要烧热水给姑娘处理伤口,还要煎药……”
“人已喝过药,伤口我来清理,你去包粽子。”祝眠慢悠悠晃到床边坐下。
“热水……”
“动作快点,我很饿。”
这句话说得短促,惊得小赵浑身一抖,连声应着跑下了楼。
软玉楼内余下的姑娘们悄悄探头出来,瞧到枯坐禅的门虚掩着,没人敢上去一探究竟。
热水送上楼时,祝眠仍在床畔坐着,手边多了堆长长纱布条。再一瞧,他已换上身绸缎衣裳,是件合身的霁青色长衫,原是儒雅中透着贵气,但袖摆被他结了个疙瘩在小臂下坠着,便显得不伦不类。
小赵将水盆放好,再飞速下楼,又提一桶热水上楼。再回屋内一看,小赵安心许多,放下水桶悄声离开,钻进厨房里包粽子。
枯坐禅中,祝眠将被褥尾端掀开一角,露出一双伤痕累累的脚。
曾踩在人皮鼓上起舞的双足,此时血迹斑斑,夹有泥污。
他挪挪位置,将这双脚抬起,落在自己大腿上,随后扯块布条在热水盆中浸湿,小心翼翼地擦去脚上血污、泥土。一遍遍擦拭后,盆中水逐渐浑浊,泥
本章未完,点击[ 下一页 ]继续阅读-->>
【本章有错误,我要提交】【 推荐本书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