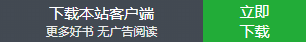1.
田学军回村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这么大的压力。这种压力不同于简单的是或非的问题,有些基层工作的实质就是模棱两可,这中间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对,什么是错,标准答案只有自己去寻找,有时候找寻到的答案是无果,但无果有时候就是最好的答案,或许正如鲁迅先生说过的,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”
走到十字路口,大门开着,一眼就看到陈祥家外院子门前冲大路的那棵枣树,上面挂着一串铜铃铛,一阵风吹过,铜铃铛发出“叮当、叮当”的金属音,大门上依旧画着八卦图,还有门框上面那块黑压压的石头。
田学军不喜欢这种刻有符篆的石头,甚至这所谓的驱魔铃铛和八卦图。人生四十多年,田学军走过很多的地方,西藏当兵那会儿,见过当地老人手里一直摇的转经筒,湖边悬挂着的五彩经幡,和一块块石头上刻着的经文,虽然这些就是一种纯粹的信仰,但田学军一直都不喜欢,在田学军的世界里就是:老婆孩子热炕头,有土地有庄稼,幸福的生活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,又有什么理由轻生呢?轻生了又有什么理由缠着活人不放呢?或许这就是执念吧!活着的人有执念,死了的人也一样有执念。
大门敞开着,一定是陈玉山来了侄子家。
陈玉山是个怪人,一辈子不务正业,轰鸡撵兔,捕鱼捉虾,竟然对女人也没有爱好,自己住在大冢子山里,也不大同外人交往。现在大冢子山上连他一共还有三户,包果园的黄书才和陈玉存,那陈玉存是他堂叔家的弟弟,他爸就是当年陈家的执事人——陈茂堂,再有就是陈玉山了。陈玉山很少同陈玉魁家来往,亲弟兄更像陌路人,特别是有陈祥他娘在的时候,连过年兄弟俩都和不到一块去,陈玉魁的死他更是对陈祥母子耿耿于怀。
但说来奇怪,人老了,反而有了变化,特别是这两三年,他对陈祥却不同往年了,竟然逢年过节的时候,给侄子送到大门口捕捉的兔子和山鸡了,陈祥沉默的像个死人,村里没人和他来往,有一次他孩子发烧烧迷糊了,他媳妇找不到帮忙的人,去山上喊了陈玉山下来,没想到陈玉山竟然抱起孩子就跑,一直跑了二十里山路送到了镇卫生院里。从那以后陈祥媳妇对他这个大爷略好了些,但陈玉山终究是心里有些芥蒂,没事从不踏进陈家老宅子半步,这一次一定是他侄媳妇交待了他什么,他才打开了院门。
“玉山哥……玉山哥……”
田学军走进了内大门的院子,一边喊着陈玉山的名字,一边用眼睛打量着院子。
田学军很少进这个院子来,印象中也就一两次,陈祥是个“闷油葫芦”,不同人言语,村里找他家有事就是在内院门口喊几声,他媳妇就出来迎着,一般这个家庭有什么事情都是女人当家做主。
主人不在家,院子里冷清了许多。田学军自打进了院子,眼神就不自觉地朝西瞥着,这个院子西边树底下有两个并排在一起的房子,一个是‘圈’(农村卫生间和养鸡鸭共用的地方),一个是起脊的房子,‘圈’有一个幽深黑暗的栅栏门,栅栏门只有门框一半高,透过裸空着的那一部分就能看到圈里边,圈里边一半透着光线,见不到光的那一半就黑洞洞的,挨着圈的北边是个狭长的房子,那个房子大白天拉着窗帘,说不出的诡异。
田玉山知道陈祥的娘就死在了那个栅栏门里,被他爸用铁榔头砸死的,北边的狭长房子的窗帘后边,就住着那几个寻短见的鬼,想到这里,田学军忍不住多看了两眼,就在他出神的那一刻,堂屋的门开了,并传来了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:
“谁呀?”
门推开了,出来了一个略有些猥琐的五十多岁的男人。那个男人个子不高,头发乱蓬蓬的,一双细长的眼睛下面有一个尖尖的下巴颏,酒糟鼻子,颧骨微隆,浑身上下脏兮兮的,似乎透着一身酒气,也许中午自己在家喝了一点,这个家里应该很少有人来,所以那人慢吞吞的从屋里走了出来。
当他看清来人时,似乎有点出乎他的意料,忙揉了揉眼睛说:“噢,是学军啊,怎么,有什么事么?”
“噢,我看院门敞着,我就过来看一下。”田学军笑着同那个男人说话。
“祥子和他媳妇不在家,有什么事他过几天就回来了。”
这个人就是陈玉魁的大哥、陈祥的大爷——陈玉山。陈玉山显然注意到了田学军瞅着西边房子发呆的眼神,说话间露出了不太欢迎的口气。
“哈哈,玉山哥,这不老许让祥子去住几天院,检查检查,这老许啊,也是挂念着祥子,想着这次给祥子调调脾气,给他在县城找份工作,也不能一个大男人,总在家憋着你说是吧玉山哥。”
田学军这样的一番话,似乎缓解了气氛,陈玉山的神情不那么抵触了,从廊厦后边拽出了两个马扎,招呼着田学军就在院墙根坐下了,说:
“是呀,眼瞅着他的孩子也六七岁了,玉魁走的时候祥子比他孩子大不了多少。”显然,陈玉山对陈祥他妈还有很深的隔阂,话里话外绝口不提她的名字。”
“希望这次陈祥能好起来玉山哥。”田学军努力寻找着话题。
陈玉山掏出了一颗“宏图”烟,狠吸了一口,吐出了烟雾,然后用左胳膊支住膝盖,用手抹了一把脸说:
“祥子没毛病
本章未完,点击[ 下一页 ]继续阅读-->>
【本章有错误,我要提交】【 推荐本书】